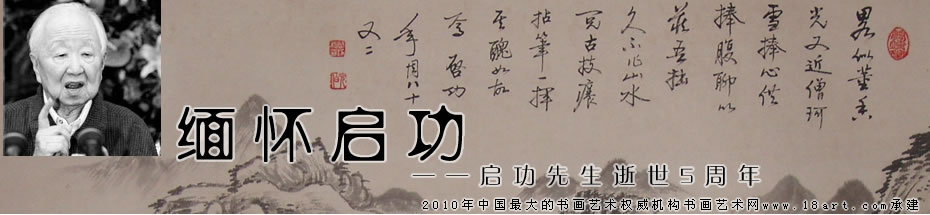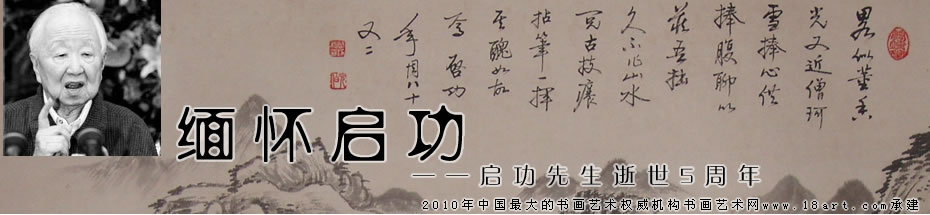再过二十多天,我国著名国学大师、书画大师、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启功先生就将迎来自己93岁的寿辰;然而,这位一生攻克了无数学术堡垒的老人却最终没能战胜病魔,昨天凌晨2时25分,一代学术大师启功先生因病在北大医院与世长辞。
启功先生一生在北师大的执教生涯超过70年,他用严谨求实的治学方法,循循善诱的长者风范,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人才,启功先生也用自己的行动实践了他为北师大提出并题写的百年校训———“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同时,先生一生笔耕不辍、著述颇丰,即使晚年受眼疾影响,书写困难,但仍坚持口述录音,请别人整理,不断有学术新篇问世。去年92岁寿辰之际,他还一连推出了《启功口述历史》、《启功讲学录》、《启功韵语集(注释本)》、《启功题画诗墨迹选》以及由自己题跋的《董其昌临天马赋》共5部新著。
据北大医院干部重症监护病房的宋主任介绍,启功先生病逝的原因主要是多脏器衰竭,此前老先生曾有反复的肺部感染,后因为脑血管病导致昏迷。今年春节后,启功就一直住院治疗,经过抢救曾一度病情稳定,后又有反复并逐渐加重。上周住进重症监护病房并用上了呼吸机。由于年老体弱,最后呼吸衰竭。
杭州作出反应
●启功先生是西泠印社的一个标杆
●孤山社址的“柏堂”今起设置纪念灵堂,向公众开放
采访西泠印社
昨天,西泠印社已经给启功先生治丧委员会发去了唁电,随即又召开了社长会议,成立了以常务副社长郭仲选为主任的追思委员会,定下了纪念启功的各项活动:今天在孤山社址的柏堂,启功先生的纪念灵堂对外开放;印社将派代表参加启功先生治丧委员会,选派副社长级代表进京参加北京悼念活动;7月5日下午3点,在杭州新侨饭店举行启功先生追思座谈会。
西泠印社副社长陈振濂通过杭州日报宣布,柏堂将接受西泠印社以及包括杭州市民的悼念及挽联,“能在这里追悼一位国际级的文化名人,也是杭州的一件大事”。
陈振濂告诉我们,在这种沉重的时刻,只有杭州才足够以发出这样的声音。“启功先生与西泠结缘将近有25年的历史。在上世纪80年代初,他就受到当时西泠印社社长、好友沙孟海先生的邀请来杭,参加西泠印社的雅集活动。此后在25年时间里,启功先生不断关心、支持西泠。在第五任社长赵朴初去世之后,西泠印社代表赴北京,希望启功先生能够在赵朴老之后担任西泠社长一职,他欣然应诺”。
2002年,在西泠印社六届五次理事会上,印社中人一致选举由德高望重的著名书画家启功先生担任第六任社长。此后在西泠印社的活动中,启功先生是一面不可缺少的旗帜。但是因为启功在北京的活动越来越多,以及健康原因,启功担任社长以后一直没来过杭州,这成为启功先生和西泠印社的一大遗憾。
筹办百年社庆时,陈振濂对启功先生的回忆是这样的:“启老说,100年,人生一辈子难得碰到这样的盛事,但是由于身体原因,终未完成夙愿。他托人送来‘百年名社,千秋印学———贺西泠印社百年华诞’的书法贺礼。如今这块镌刻着由他题写、左下角盖有启功名印、右上角刻着‘金石缘’一印的巨石就坐落在孤山脚下。”
虽然启功先生担任社长后一直没能来杭州,也没有参与实质性的工作,但陈振濂告诉我们,“身任社长一职,启功先生本人就是西泠印社的一个标杆。启功先生在学术、艺术创作上的造诣对于西泠建设名家之社、博雅之社就是非常直接的证明”。
从吴昌硕到赵朴初、启功,西泠印社的社长人选,早已有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必须是一名学术泰斗、艺术大师、文化名人。西泠印社的下一位社长会是谁?一切不得而知。不过有理由相信,西泠印社掌门人的岗位肯定会有一段较长时间空缺,因为从2000年西泠印社第五任社长赵朴初去世到2002年请来启功先生担任社长,这个重要的岗位整整空缺了两年。
拍场作出反应
●启功突然离世,其作品的价格暂时不会出现很大波动
●新的书法主流有待于形成,而市场共识的达成、市场新主流的培育都需要漫长的时间
原先,在世书家中,启功先生无疑是最“牛”的一位,他的作品在市场上极受海内外藏家的青睐和追捧。
以2003年北京春拍为例。中国嘉德共推出10幅作品全部成交,最低的为《临米芾书法》镜心,尺寸仅为22.5CM×44.2CM,成交价高达2.2万元,换言之每平方尺高达2万元以上;另外超过8万元的有4幅,其中《行书唐宋诗七幅》镜心被拍至41.8万元,其成交价令人咋舌。另外,北京翰海推出的10幅作品也全部成交,华辰9幅作品成交8幅,荣宝5幅作品全部成交。其市场价值可见一斑。
浙江皓翰拍卖·董事长蒋频———
“启功先生的书法流传到市场上的很多,真正的好东西并不多。收藏家都会更为关注他的代表作品。他的突然去世,暂时还不会使其作品的价格出现很大的波动,这还有待时日。
“一位主流的书家去世了,传统书风损失了重要的领袖人物,势必会影响到书法市场、书法风气,这也一定能拉动当代书法的价位。因为在艺术品市场里,与绘画作品相比,书法作品的地位一直不高。”
西泠印社拍卖公司·总经理陆镜清———
“启功先生的作品在北京的拍卖中很多,但是出现在浙江拍场的却还为数不多。现在他的作品不可能再生产,那么市场存量只是现有的部分,肯定会发生收藏和拍卖价值的变化。一位著名艺术家顶峰的作品已经很珍贵,而其代表性的力作更为稀少,因此启功先生的作品作为收藏品已经是珍品。即使是价格不在短期内冲高,也不会影响其艺术价值的珍贵和他本人在美术史上的重要地位。”
北京荣宝拍卖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刘尚勇———
“一个主流的书家去世了,传统书风损失了重要的领袖人物,书法市场、书法风气,必然会发生一些变数。这意味着新的书法主流有待于形成,而市场共识的达成、市场新主流的培育都需要漫长的时间,如果市场共识发生动摇、混乱,失去方向感,书法市场可能会因此沉寂一段时间。”
由于启功作品在艺术市场上价位较高,也就成为一些利欲,心者摹仿伪造的对象。目前,启功的伪作已呈泛滥之势。
如何鉴别真伪启功书法
辨别启功书法的真伪,除了要看他特有的瘦硬笔法、内紧外松的结构,以及典雅脱俗的书卷气外,从作品钤印上往往也能看出造假的破绽来。
启功先生的常用印章并不多,大约有十几方,经查阅统计,有阴刻长方形印“启功”、阴刻方形印“启功”、阴刻方形印“启功之印”、阴刻方形印“启功私印”、阴刻方形印“功在禹下”、阳刻长方形印“长庆”、阳刻方形印“元白”三方、阴刻“启予子”等。这些印章均出自篆刻名家之手,主要有王福庵、刘博琴、金禹民、熊伯齐。
一些书法造假者往往重视启功书法的摹仿,却忽略了作品上用印的精到,有的虽然重视了,但由于方寸之石,全在细微之处显示精妙,功力不深,难以达到原印神韵。
从印章上鉴定书画真伪常常是有效的,鲁迅先生就曾看出印章中刻错了字,而认定一件书法为赝品的。
“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瘫趋左,派曾右。面微圆,皮欠厚。妻已亡,并无后。丧犹新,病照旧。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渐相凑。计平生,谥曰陋。身与名,一齐臭。”
———启功《墓志铭》,写于66岁那年
以白描的方式告诉人们这是一个可爱的老头
那一段幸福的包办婚姻
启功的婚姻不仅要遵“母命”,还要按清代传统只在旗人内部论亲。他21岁时中学毕业,正忙于四处求职,在母亲的包办下,便与从未见过面的章宝琛成婚了。
章宝琛不通文墨,而且是带着可怜的小弟弟一起嫁过来的。但自她来到启功家后,任劳任怨,再不要启功为“家”操心,使启功对她由“同情”逐渐转化为“爱情”。
他曾经说:“我的老伴儿比我大两岁,也是满人,我习惯地叫她姐姐。”
1975年春天,“姐姐”病倒了。得知妻子已时日不多,启功失声痛哭。
他曾经这样写道:“她撒手人寰后,我经常彻夜难眠。当年我和妻子曾戏言如果一人死后另一人会怎样,她说如果她先死,剩下我一人,我一定会在大家的撺掇下娶一个后老伴儿的,我说决不会。果然先妻逝世后,周围的好心人,包括我的亲属都劝我再找一个后老伴儿。还有自告奋勇,自荐枕席的,其牺牲精神令我感动,但我宁愿一个人,也许正应了元稹的两句诗:“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京片子·京油子
在北师大校园内,“师”门弟子爱戴、尊敬启老,见面总爱称他为“博导”。启功便言:“老朽垂垂老矣,一拨就倒、一驳就倒,我是‘拨倒’,不拨‘自倒’矣!”
在他被任命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后,有人祝贺说,这是“部级”呢。启功则利用谐音风趣地说:“不急,我不急,真不急!”
更为幽默风趣的是启功外出讲学时,听到会议主持人常说的“现在请启老作指示”,他接下去的话便是:“指示不敢当。本人是满族,祖先活动在东北,属少数民族,历史上通称‘胡人’。因此在下所讲,全是不折不扣的‘胡言’……”如此见面语,立马活跃了会场气氛。
我不姓爱新觉罗我姓”启”,名“功”
启功生前接受采访时说,我既然叫启功,当然就是姓启名功。
但偏偏有人给他写信,爱写“爱新觉罗·启功”收,开始他只是一笑了之。后来越来越多,他索性标明“查无此人,请退回”。
启老说,确实啊,不信你查查我的身份证、户口本,以及所有正式的档案材料,从来没有“爱新觉罗·启功”那样一个人。
虽然启功不愿称自己是爱新觉罗,但他确实是清代皇族后裔,属正蓝旗。他说:“我是雍正皇帝的第九代孙。雍正的第四子名弘历,他继承了皇位,这就是乾隆皇帝。雍正的第五子名弘昼,只比弘历晚出生一个时辰,当然他们是异母兄弟。乾隆即位后,封弘昼为和亲王。我们这支就是和亲王的后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