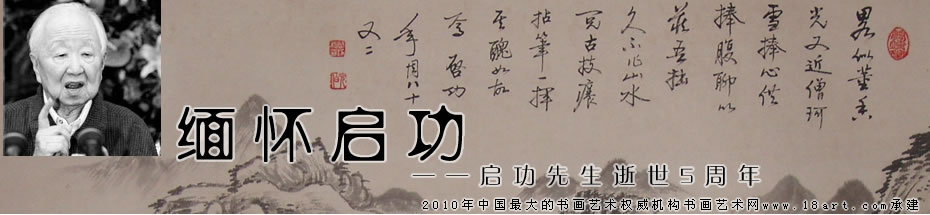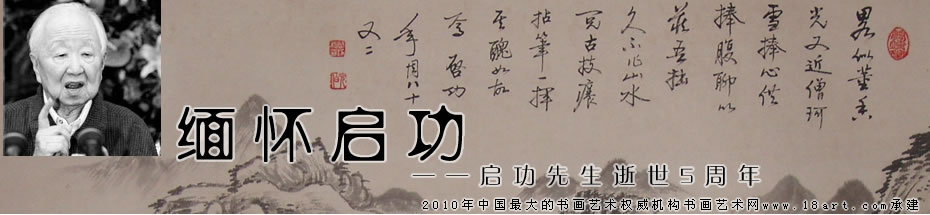启功的贤妻有一颗金子般的心。妻同他共渡患难,历经五七年反右与“文化大革命”的煎熬,最后竟先他而去,给启功留下了无限的怀念。
在启功的心底,一个永远不能忘怀的人是他的妻子章宝琛。
她长启功两岁,23岁与启功结婚,到启功63岁时的1975年去世,骨灰埋在启功妈妈和姑姑的墓旁。
20世纪30年代初,启功21岁的时候,母亲向他提出一门亲事。启功家是旗人,按清代传统都得在旗人内部论亲。
启功当时正忙于寻找职业,根本没有结婚成家的念头,忙对母亲说:“我现在事业还没个定向,为什么要这么早结婚呢?”母亲说:“你父亲死得早,妈守着你很苦啊,你早结了婚,身边有个人,我也就放心啦。”启功是个很孝顺的儿子,母命难违,启功考虑了一下便对母亲说:“行啊,人,只要妈看着满意就行啦!”
1932年,启功20岁时,母亲和姑姑为他相中了一位叫章宝琛的姑娘。
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启功家祭祖的日子——1932年3月5日,母亲和姑姑便叫章宝琛过来帮忙。母亲对启功说:“宝琛该来了,你到胡同口去接接她。”当时天空中飘着绵绵细雨,启功来到胡同口,看见对面林阴小道上,一位女子撑着把花伞,迈着莲花碎步,正袅袅娜娜地向他这边走来。启功的心顿时像被一只温柔的手摩挲了一下,不由轻轻地吟起了戴望舒的《雨巷》,这位女子不就是《雨巷》中那个丁香一样的姑娘吗?
姑娘来到跟前,启功轻轻地问:“你是章宝琛?”她抬头看了启功一眼,羞涩地点点头柔声问:“你是谁?”“我是启功。你比我想象中可爱、漂亮得多。”两片红霞倏地飞上章宝琛的脸颊,使她显得更加妩媚动人。
1932年10月,启功和章宝琛举行了简朴的婚礼。
虽说是新婚燕尔,却实在没有什么感情可言,因为原来没什么恋爱过程,只见过个把次面。可是渐渐地启功发现,这位文化不高的妻子竟是一位难得的知己。
章宝琛由于生母早亡,父亲续弦,后妈对她非常刻薄,从小就吃了不少苦,她是带着同她相依为命的弟弟一起嫁过来的。当启功了解她的身世以后,强烈的同情心逐渐化成了爱恋之情。
章宝琛个子矮矮的,眼睛大大的,皮肤白白的,样子端庄贤惠,爱穿一件蓝布衣衫,最可爱的是她从不发脾气,她勤劳、善良、贤惠,具有中国妇女传统的美德。启功有时发脾气,她却从不言一声,很厚道,什么都忍受。
刚结婚,住在前马厂的鼓楼时,家里常有聚会,常来的有曹家琪、马焕然、熊琪,还有张中行。那时,启功的家一进门就是一个炕,地方很小,他们坐在炕上一侃就是半夜,启功的妻子站在炕前一言不发,一宿都侍候大家端壶倒水,从不插言。后来搬到黑芝麻胡同,再后来又搬到小乘巷,章宝琛弟弟的家住在四合院的两间南房。现在在启功家照顾启功的章景怀和郑喆就是她的侄子和侄媳妇。
自从新媳妇进门之后,家里的一切大事小事都无须启功操心。早晨一睁眼她就默默地干活,把一切操持得井井有条,无论多么累,从来没有一句怨言。
母亲和姑姑上了年纪,又常闹病,不免时常发脾气,可是不管遇上多少委屈的事,她从来不顶一句嘴,有时实在委屈就一个人躲在角落里偷偷掉泪。启功有时在外面碰上不顺心的事,回家来也常冲她发脾气,可是,每次都是一面官司,妻子总是不言语,想吵也吵不起来。有多少回启功看见妻子独自躲在小屋里啜泣,看来这是她抒发心中委屈的唯一法子了。
1956年,启功母亲久病不起,弥留之际,拉着儿媳妇的手说:“我只有一个儿子,没有女儿,你就跟我的亲闺女一样。”母亲死后,启功悲伤中想起妻子日夜侍奉老人的辛劳,想到她深明大义,对自己体贴入微,照顾十分周到,对她十分感激。启功曾十分激动地对妻子说:“你跟着我没过上一天好日子,我应该多受些苦才对得起你。”说着忍不住双膝跪下给妻子磕了一个头。
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启功被划成“右派”分子。回家来,夫妻相对默默无言。妻子不解地问:“他们怎么会找到你当这个‘右派’呢?”
启功说:“这个你不知道,我参加过土改,划什么分子都有比例数,这个‘右派’也是有比例的,既然有比例,就有倒霉的,我就是倒霉的。”妻子还是不解地问:“可你除了教书、写字、画画,又干什么来着?”
启功想了一下说:“你想想,这不是明摆着,咱们是封建家庭,受的是层层的封建教育,连资产阶级思想都够不上,何况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呢?划我‘右派’也不屈,宰了我也当不了‘左派’啊!”只有一点启功想不通:“‘右派’就‘右派’吧,干吗还要加分子!”妻子见他那抱头痛苦的样子,就紧紧抱住丈夫,泣不成声:“那么苦的日子我们都挺过来了,还有什么能难倒我们?如果你有个好歹,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她劝启功说:“谁批你,骂你,你都不要怕,陈校长知道你是个好人,我也知道你是个好人。”她深知启功爱讲话,“烦恼皆因多开口”,就经常把自己的经验告诉他:“有些不该讲的话,你要往下咽,使劲咽着……”
在困难的时候,愈加显出妻子的一颗金子般的心。当启功被莫名其妙地划为“右派”而心灰意冷的时候,妻子也学着陈垣校长的样子劝说他埋头写书,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现在没人给你出版,总会有拨云见日的一天。启功听了妻子这些朴素的话,心头荡起一股暖流,解开了心头的死结。
当生活拮据的时候,妻子便把珍藏的首饰拿出去典卖,换得钱做点好吃的,留着启功回来吃。她知道启功经常需要添置新书,每月生活再紧,她也总要留出一部分钱给启功买书用。
正当启功全力以赴在学术上进行冲刺时,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他再次被迫离开讲台,一切公开的读书、写作也被迫停止。经历了太多的风风雨雨,启功内心出奇地平静。他想,不让我公开读书写作,我就私下里治学。为了让启功能够专心在家撰写文章,章宝琛天天坐在门口给他望风。一见红卫兵,她立即咳嗽,启功马上把纸和笔藏起来。一次,造反派来抄家,什么也没查到,便问启功:“你家有‘封资修’的东西吗?”启功说:“‘资’没有,‘修’也没有,就是有‘封’。”几个好心的学生有意掩护地说:“好吧,那就给你封上吧!”在门上贴了一个封条:“启功家已查封”。这样,他和妻子就更安心了。
“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抄家,细心的妻子偷偷地把启功宝贵的藏书、画和文稿用纸包了一层又一层并打上捆,放在一个缸里,在后院的墙角下挖了一个洞,深深地、深深地埋在土地的深处———神不知,鬼不觉,就连启功也没告诉。
1975年,老伴积劳成疾一病不起,她临去的时候,才把藏书、画、文稿的地方告诉了启功。启功到后院挖啊、挖啊!挖出来打开一看,那些凝聚着多年心血的文稿,被用一层又一层的纸包裹着,连一张也没丢。
老伴去世后,1979年,北师大党组织正式为启功平反,宣布“右派”系错划。为他加了一级工资,他让给了更加需要的人。问他有什么意见,启功喟然叹曰:“改与不改,对我都无所谓了。”那位同志愕然问:“为什么?”启功说:“当初知道我被划为‘右派’分子特别为我揪心的两个人,一个是我师陈垣,一个是我老伴,现在,这两个人都不在了……”说至此,不禁潸然泪下,老伴与他共同生活了四十多年,除了吃苦受累,提心吊胆,没过一天好日子,今天,终于直起腰来了,她却永远离开了他……
启功的老伴唯一的遗憾是他们没有孩子,她一直执著地认为是自己的过错。启功在辅仁大学教书的时候,经常和女学生去看展览。亲戚中一位老太太好意地问她知道不知道,没曾想她反而对那位老太太说:“不说他不会有问题,就是他有问题我也无怨言,我希望哪个女人能给他留下一男半女,也了了我的心愿!”她的善良已经到了超自我的程度。
1975年,老伴临走的时候,除了告诉文稿的藏处外,还嘱咐启功说:“我死了以后,你一定要再找个人照顾你!”
启功听后说:“老朽如斯,哪会有人再跟我?”
妻子说:“你如不信,可以,赌下输赢账!”
启功说:“将来万一你输赌债怎么还?”
妻子说:“自信必赢,且不需债还钱!”
妻子死后,做媒人四面八方来,启功先生不同意,介绍人竟来查房,见是双人床,说,启功肯定有意。启功知道以后,干脆把双人床换成现在用的单人床。
启功先生的好友张中行先生评价说:“像启功的好老伴,世上没有超过她的,再怎么找,也找不到的!”
其实,这不是说启功自己赢了输赢账,而是永远不能忘怀的真情难抛,他在一首悼亡诗中写道:
先母晚多病,高楼难再登。
先妻值贫困,佳景未一经。
今友邀我游,婉谢力不胜。
风物每入眼,凄恻偷吞声。
启功不止一次对朋友说:“我这一辈子有两个恩人,一个是陈垣老师,一个是我的老伴。但他们两个都是为我窝着一口气死去的。老伴在时,连现在看来极普通的要求,我都没能满足她,她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她虽死而无怨,我却心里更加难受。我们是‘有难同当’了,却不能‘有福同享’。”
“因此今天我的条件越好,心里就越不好受,特别是我今天得到的一切,已经觉得名不符实了,怎么能安心地享受这一切呢?况且我已无父母,也没有兄弟姐妹,又无儿无女,身内之物一件都没有,我要钱、要物、要名、要那么多身外之物还有什么用呢?我只有刻苦一点,心里才平衡一些。” 摘自《启功杂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