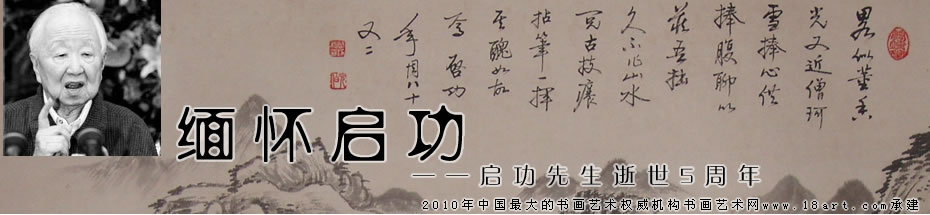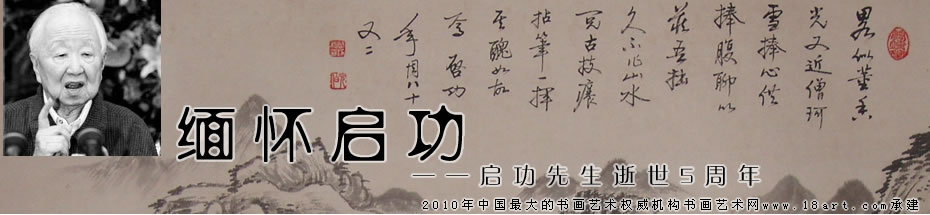一个年少多磨的末代皇族,一段真挚情深的爱情故事,一位勤勉宽容的睿智长者,一代书画双绝的文博大家,《中国文博名家画传——启功》一书,为我们揭开有“当世第一书法家”之称的启功先生一生的风雨历程和生活中鲜为人知的故事。
少年--出身皇族 家道败落
启功出身皇族,姓爱新觉罗。其始祖,是清代雍正皇帝的第五子弘昼(乾隆皇帝是排行第四的弘历),被封为“和亲王”。启功1912年生于北京。年幼时,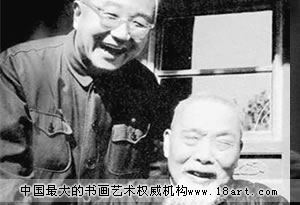 祖父疼爱他,让他拜雍和宫的老喇嘛为师。于是启功就成了教名为“察格多尔扎布”的记名小喇嘛。长辈希望他能得到“金刚佛母”的保佑,但是,启功1岁丧父,10岁时又失去曾祖父、祖父。因偿还债务,家道已经败落得一贫如洗,以致启功无力求学。在曾祖父门生的帮助下,他才勉强入校学习。 祖父疼爱他,让他拜雍和宫的老喇嘛为师。于是启功就成了教名为“察格多尔扎布”的记名小喇嘛。长辈希望他能得到“金刚佛母”的保佑,但是,启功1岁丧父,10岁时又失去曾祖父、祖父。因偿还债务,家道已经败落得一贫如洗,以致启功无力求学。在曾祖父门生的帮助下,他才勉强入校学习。
启功从小就酷爱绘画,幼时看到祖父拿着笔蘸上墨彩,在扇面上涂抹几笔,就勾勒出活灵活现的花鸟竹石。那时他便萌生了要学习画画的强烈愿望,于是也拿起了笔。尔后在祖父的引导下,他师承贾羲民、吴镜汀学习画画,且渐渐有了起色,得到了亲友们的赞许。在汇文小学读书时,启功的习作就曾被学校当作礼品赠送给友人。
当时故宫博物院开放了好几个书画陈列室,很多珍贵的古代书画作品经常轮流展览,重要作品展览的时间长一些。那时故宫的门票是1块银圆一张,每月一、二、三号减为三毛。这些展览对启功这样的穷学生有莫大的帮助,像范宽的《溪山行旅图》和郭熙的《早春图》,启功都是在那个时候仔细观摩过的。
启功十七八岁时,一次一位长辈让他画一幅画儿,并说要装裱之后挂起来。启功感到十分光荣,但那位长辈又对他说:“画好后千万不要落款,请你的老师代你落款。”这意思很明白,就是看不上他的字。这对他刺激很大,启功从此暗下决心,发奋练字,几十年来刻苦钻研,始终不渝,终成一代书法大家。
青年--三进辅仁 幸遇恩师
1933年,21岁的启功笔下的书画文章,却有了佼佼之色。祖父的门生傅增湘拿着启功的作品,找到了当时辅仁大学的校长陈垣。傅增湘回来后,喜滋滋地告诉启功:“陈垣先生说你写作俱佳。”他嘱咐启功去见陈垣,并强调说,要向陈垣先生请教做学问的门径,傅增湘告诉他:找到一个好老师,比找到一个职业还重要,那将终生受用不尽。
陈垣帮启功找到了在辅仁大学附属中学教国文的职业,从此以后,启功就始终没有离开过教育岗位,为祖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启功认为“为人师表”是世上最高尚的事情。
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谢学锦先生,就是启功在辅仁大学附中教过的一名学生。谢学锦回忆说:“我放眼看世界,就是在初一年级国学老师启功的熏陶下开始的。启功老师讲课生动,引人入胜。在他熏陶下,我对文学发生了极大兴趣,不仅学习课本上所选的诗、词、文、赋及小说片段,还到图书馆去借阅各种文学书刊。”家境贫寒的启功,能有这份工作实属不易,可是,虽然他兢兢业业地教书,还是被辞退了。理由很简单,当时辅仁的校长认为他中学没有毕业,怎能教中学?工作不到两年就失业,这对初次步入社会的启功来说,无疑是个很大的打击。
1935年,经陈垣介绍,启功又在辅仁大学美术系担任助教。掌管美术系大权的教育学院院长,还是两年前那位中学校长。两年后,启功再次被他以“学历不够”为名解聘,启功又失业了。
当时北平正值沦陷期,在日伪控制下,物价飞涨。为了生活,启功不怕辛苦,分别在两家人家教家教,辅导他们的孩子准备考小学和中学,以换取微薄的报酬维持全家生活。他闲时集中精力在家中读书,或研究书法绘画。这时他的作品已经在社会上小有名气,间或作画卖画,以补贴家用。
陈垣得知启功再次被解聘的消息后,坚信启功是个有真才实学的青年,不应被埋没。他再次向启功伸出援助之手,再次安排启功回到辅仁大学。1938年秋季开学后,陈垣聘启功教大学一年级的“普通国文”。这是陈垣亲自掌教的课程,终于再也没有人会解聘他了。要不是陈垣先生的慧眼识才,一而再、再而三地聘用,就不会有今天的大学问家启功。
启功到辅仁大学教大一国文时,决心似铁,教育家陈垣更是古道热肠,他告诉启功应该在教每一课书前,都要准备得非常熟练。启功有幸能到陈垣校长授课的课堂上亲聆教诲,观摩启发式的教学方式,看漂亮实用的板书。后来启功说:“当时师生之友谊,有逾父子。”
中年--划为右派 手抄著作
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了,已入“不惑”之年的启功,正值事业、学问、艺术几近炉火纯青之时。启功身为北京师范大学的教授,运动初期,在本校并没什么问题,但是1958年却戏剧性地在中国画院被扣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右派关系转到北师大后,启功已经被评定的教授职称被取消,薪水也降了一级,那时他的母亲和姑姑刚刚去世,对启功来说,这无疑是雪上加霜,是极为沉重的打击。
启功最困难的时候,陈垣一次在琉璃厂,偶然发现有几张明清画卷,他知道这些字画是启功最心爱之物,启功既然把心爱之物都卖掉了,想必经济十分拮据。陈垣当即买下这些画,并派秘书去看启功,带去100元钱。恩师的关怀和鼓舞,让启功在逆境中坚持下来,并在学术上有所建树。1959年,启功“右派”的帽子终于被摘掉了。
右派分子不能再上讲台,启功下决心,要在艺术和学术上做些贡献。于是,他利用“劳动改造”的业余时间,潜心于学术研究。读书,写文章,集中研究他所喜爱的诗词曲赋及骈文的韵律声调。启功根据多年的研究心得撰写了《诗文声律论稿》。这部著作从1961年开始构思,到“文化大革命”中,经多年的反复推敲和修改,书稿已经有一尺多厚,但是那个时候学者出一本著作谈何容易,书稿放在家里,启功不放心。“文革”中流行工农兵集体创作,他怕被充为公共财产。启功终于想了一个办法:他找来最薄的油纸,晚上在灯下用蝇头小楷抄写,尽量压缩字数,终于完成一部六万字的手抄本,如有紧急情况,随时可以缠在腰上带走。这部《诗文声律论稿》直到1977年“四人帮”粉碎后,才由中华书局出版。
婚姻--寄人篱下43载
1932年,在母亲与姑姑的“安排”下,启功与章宝琛女士完婚。章氏也是满族人,比启功大两岁。他们婚后夫妻情深,是典型的婚后恋爱,他们的爱情是真挚、纯洁、深沉、持久的。
1962年,启功重新登上了讲台,这段时期,他撰写了《古代宋字体论稿》、《诗文声律论稿》和《红楼梦札记》等学术专著,在学术上取得了重大成就。正当启功全力以赴在学术上进行冲刺时,1966年“文革”爆发,他再次被迫离开讲台。为了让启功能够专心在家撰写文章,章宝琛天天坐在门口给他望风,一见红卫兵,她就立即咳嗽,启功则马上把纸和笔藏起来。
在启功接受为《清史稿》加标点任务的1971年,章宝琛由于常年的贫困生活积劳成疾,患上黄疸肝炎。1974年,章宝琛病情加重,尽管启功一再对妻子隐瞒她的病情,聪慧的章宝琛却早已从丈夫的神态中看出来。她伤感地说:“启功,我们都结婚43年了,要是能在自己家里住上一天,该多好”是的,都43年了,他们一直借住在亲戚家,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第二天,启功开始打扫房子,他决定马上搬家。傍晚,当他收拾好东西赶到医院时,妻子已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妻子走后两个多月,启功搬进了学校分给他的房子,他终于有了自己的家。他怕妻子找不到回家的路,便来到妻子坟头,喃喃地说:“宝琛,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你跟我回家吧。”回到家里,启功炒了妻子最爱吃的几个菜,他不停地给妻子碗里夹菜,当妻子碗里的菜多得往桌上掉时,启功趴在桌上失声痛哭……
悲愤间,启功写下了在书报杂志和互联网上广为流传的那首看似戏言的《自撰墓志铭》:
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瘫趋左,派曾右。面微圆,皮欠厚。妻已亡,并无后。丧犹新,病照旧。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渐相凑。计平生,谥曰陋。身与名,一齐臭。
启功一生无儿无女,妻子去世后,他一直过着孤独而清苦的生活。他把卖字画和稿费所得的200多万元人民币全部捐给了北京师范大学,而自己却住在简陋狭小的房子里。
如今,启功先生已90岁高龄了,每年的清明节,他都坚持去墓地“带”妻子回家。他对身边的亲属说:“要是我走了,就把我与宝琛合葬在一起。我们来生还要做夫妻。”
逸事 启功不“打假”
有一次,启功到荣兴画廊参观,见画摊上摆满名人字画,有赵朴初、董寿平和他自己的作品,每个摊位上都有,有的还在批发。一位摊主是老太太,看到启功来了,就对旁人说:“这个老头好,这个老头不捣乱。”(意思是不找他们的麻烦)启功先生知道市面上假冒他的名的赝品很多,不少朋友建议追查,他却不同意。有一位年轻人写了一封长信,对这种现象给予批评,并建议启功先生追查。启功先生给这位年轻人回了信,大意说有些假字比启功自己写的还好;而且人生几何,身后如果有人伪造,也无可奈何。他还谈到,如果自己的字都写得和二王、颜、柳甚至苏、黄、赵、董一样好,作伪也要难上若干倍,其伎俩就容易暴露,自己也可省下诉讼费了。启功先生这种博大的胸襟和自勉的精神令大家敬佩。 (记者 王健 整理自《启功》侯刚著 文物出版社 2003年12月出版)
|